第一臺電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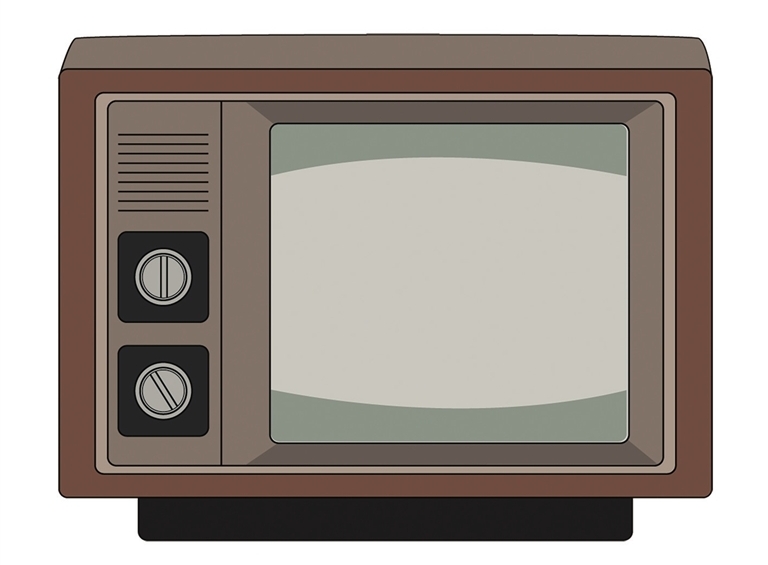
河頭的大榕樹下,河水悠悠而綿長,與它一樣綿長的,還有在河邊碼頭上洗衣服、洗菜、挑水的媳婦們的話語,從一張張嘴巴里像機關槍一樣發出來。每天早晨,這個小小的碼頭就像是村里的新聞發布會,前一天村子里的大小新聞在這肯定能聽到。
那時,我剛上小學。一天夜里,母親去接生了,天亮還沒回,家里一堆臟衣服要洗,這任務非我莫屬。我個子小,洗衣服去晚了肯定沒有好位置,就早早來到河頭,霸了個頂好的位置,那里有塊光滑的石頭可以搓洗大件的衣服。慢慢地,人越來越多,位置就有點擁擠。阿英姨來了,她是村里公認的“新聞發言人”,消息多、愛嚼舌、大嗓門……“阿麗,你往里邊去點,你個子小,站外面小心掉河里去了,我們都不會游水,撈不起你。”她一來就把我攆到靠岸邊的一塊小石頭上,霸占了我那塊光滑的大石塊。我雖不情愿,也沒辦法。
“哎哎,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昨晚我聽我家男人說,阿平家買了電視,今晚食夜(晚飯)后我們去看看啊,長這么大還沒見過電視是啥樣的。”阿英姨興奮地爆料。阿英姨老公跟阿平是穿開襠褲一起玩到大的發小,阿平買電視這么大的事肯定會立馬告訴他的。“看電視?好啊好啊,今晚早點食夜,你來我家叫我一起去,我有電筒。”阿娣第一個響應。其他的幾個年輕媳婦、姑娘,紛紛說到時要一起去看看。
在那個年代,電視機對我們村來說絕對是奢侈品、罕見品,看電視那是前所未有的新鮮事。“哪來的電視?阿平家有錢買電視?”“聽說不是新買的,是他家那個嫁到江邊村的大姐給的。他姐夫在城里干活,不知從哪兒弄來的二手舊電視。”那幾個媳婦都相約今晚要去看看熱鬧。
阿平家有電視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村。我也把這個特大新聞告訴了一起上學的鄰家兩個小姐姐,相約晚上一起去阿平家看電視。那天,我沒心聽課,放學后也沒心思干活,就巴望著天早點黑。晚飯后,母親還沒回來,我家的電筒被母親拿走了,鄰居也沒有電筒,我們三個七八歲的女娃子就趁著微微的月色,趕集似的興致勃勃地往阿平家去。
等我們趕到,阿平家已被圍得水泄不通了,床上、凳子上、門角落的木梯子上、門邊、窗戶邊,到處都擠滿了來看電視的人。兩個小姐姐死命往里邊擠,我卻怎么也擠不進人群,只聽到熙熙攘攘的人聲。不久,有人說:“別吵了,放正片了。”人群安靜下來,我在房間外面人群最外層,聽到電視里女聲唱著歌,卻聽不明白唱的是什么。我拼命踮起腳尖,還是只能看到人們的背和屁股。大約一小時后,人群終于散了,大家意猶未盡地離去。有人大聲說:“阿平,明晚留個位給我哈。”“阿麗,你在哪兒?回去了。”小姐姐到處找我。月亮應該睡覺去了,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三個會合后牽著手摸黑回家。我好奇地問:“電視長啥樣?你們看到什么了?電視里放什么?像電影那樣的嗎?”她們也回答不上,估計像我一樣,啥也沒看到。電影我們村倒是放過幾次的,電視我們都沒看過。
到家后,母親已回家,她問我去哪兒了,我如實相告,看電視去了。“看了什么片?打仗的還是其他什么故事?”我不好意思告訴母親,說除了一群人,我啥也沒看到。第二天早上,我跟母親說:“媽,上學前我去洗衣服。”我一改以往賴床的壞習慣,早早起來了,主動領了洗衫的任務。母親欣然答應,囑咐我:“小心,別往水深處站。”我答應著,歡快地挎起一籃子衣服往河頭去。大人們陸陸續續來洗衣服了。果然不出所料,她們今天的話題不再像往常那樣批判婆婆、數落老公了,而是趣味盎然地討論著昨晚的電視:“那個女演員長得真好看。”“好像是叫汪明荃。”“那是連續劇,聽說有幾十集呢,叫什么《萬水千山總是情》。”女人們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哎,那歌真好聽,“莫說青山多障礙,風也急風也勁,白云過山風也可傳情……”阿英姨竟然學著唱起粵語歌來,唱歌時她的模樣跟平時嫌棄婆婆的那副面孔判若兩人。我忽然覺得她長得挺好看的,不再是那個愛嚼舌頭的長舌婦了。那天早上,大家洗衣服洗得特別認真、特別久,總想多聽一點有關電視的話題。
第二天晚上,我和鄰家小姐姐不約而同早早吃過晚飯,天剛黑,我們就到了阿平家。阿平老婆來嫂子說:“哪有那么早,《萬水千山總是情》要八點才放,現在才七點,你們先去玩吧。”我們就找小伙伴玩去了。不一會兒,看到陸陸續續有人往阿平家去,我們也趕緊往他家跑,等我們到達,好位置又被人占了,我鉆到門角落木梯邊。電視開了,黑白色的,不知啥牌子,屏幕一直發出“沙沙”的響聲,滿屏雪花,看不到人影。“阿平,你去搖一下天線,收不到,信號不好。”來嫂子喊,阿平跑到后窗去搖那個豎立著的架子,里邊的人說:“有了有了,就這樣,別動了。”電視里有人影了,晃動了幾下,總算清晰了。我看不到電視里的畫面,只聽到聲音,索性爬到梯子上。“阿麗,你再往上爬兩級,讓我也爬上去。”下面有人推我,我又往上爬了兩級,一會兒,下面又有人爬上梯子來,就這樣,我一直爬到最上面,頭快要抵著木樓板了,弓著腰,往下看電視。角度不好,電視里的人影看不清楚,只聽到聲音,覺得那電視里的情節肯定是很精彩的,他們都看得聚精會神呢。每隔二十分鐘,就放廣告。放廣告時,來嫂子就吆喝:“梯子上的人別掉下來了哈,哎呀,你們都別坐到我床上去呀,等下床都要被你們坐塌了。”放了三次廣告,差不多有一個小時了,電視里就唱歌出字幕了,這一集就結束了。人們散去,我下了梯子來,雙手酸酸的,腳也僵僵的,一跛一拐地跟著姐姐們摸黑回家。
第三天晚上,我問母親要手電筒,她說:“不行,萬一等下有人來喊接生,我沒電筒咋辦。你去看電視,看了什么內容,好看嗎?”“第一晚沒看到,都是人,第二晚只看到電視機,沒看到內容,今晚再早點去,霸個好位置。”母親臉上閃過一絲說不出啥味道的表情,沒說話。
這次,我們又是早早到位,可是,來嫂子不開門。她說:“你們來看電視可以,每人交五毛錢電費。這電視不用電費啊?”我們沒帶錢,只好悻悻地回家了。母親見我早早回來,問:“今晚又沒位?都這么早去咯。”“來嫂子說每人要交五毛錢電費。”母親的臉沉了下去,“睡覺,以后不準去。”命令的口氣,不容我分辯半句。那晚,我帶著遺憾,輾轉難眠,腦子里總響起“莫說青山多障礙,萬水千山總是情……”那是我聽過的最好聽的歌。不知過了多久,我起床上茅廁,看到母親在挑選黃豆。“媽,你還不睡?挑黃豆干嗎呢?”“挑些好的黃豆拿去賣,你去睡吧。”
從那以后,我再也沒去過來嫂子家。
《萬水千山總是情》可能早就放完了吧。河頭洗衫的女人們再也沒討論過劇情了。那首歌,我倒是會哼哼兩句。時間悄無聲息地流逝,河水時漲時落,碼頭還是那座碼頭,榕樹還是那棵榕樹,它們就這樣靜默地注視著來來去去的人,將他們的話語、歡樂和憂愁一并收入眼底。
轉眼,我上小學三年級了。一天早上,母親囑咐我放學后要煮菜、喂豬、挑水、洗衫。她要去縣城一趟,順便挑擔黃豆去賣。傍晚放學回家,看到母親從縣城回來,挑著一擔貌似很重的東西,一頭是兩只籮筐疊在一起,一頭是一個大紙箱。我和弟弟妹妹歡呼著迎上去,對籮筐里是否有好吃的東西絲毫不感興趣,圍著大紙箱左看右看,問:“媽媽,紙箱里裝的是什么?”我可是認得字的小學生,興奮地告訴弟弟妹妹:“哇,是電視!我們也有電視啦!”弟弟妹妹兩眼放光,高興地跳了起來。
母親草草煮了晚飯,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吃完晚飯,母女幾個就拆開紙箱,小心翼翼地把電視抱出來,放在擦得干干凈凈的桌子上。我們像摸珍寶一樣摸著電視機的外殼,兩邊和頂部是褐色的、光滑的木質板,后面是黑色的、凸起的大屁股,前面是白色的屏幕。母親說屏幕不能用手去摸,會刮花的。我們催促母親快點安裝。只見她按說明書安裝好兩條天線,放在電視機頂部,拿出配套的變壓器,連接電線,插上電源,打開開關,電視里顯示兩個大字“金星”。母親說這是“金星”牌子的,是質量最好的黑白電視機,我們買的是17英寸的,還有21英寸、29英寸,還有更大的,那些要好多錢的,我們買不起。等你們長大了掙錢了再買大的。我們姐弟幾個都使勁點頭答應著,只催促母親快點快點,要放正片了。調整好天線,我家第一臺電視馬上就正式開播了。
關于看電視,母親給我們定了規矩:只有母親才能開電視,其他人不準開(父親在外地工作);當天作業、家務沒做完,不準看電視;考試不及格、被老師批評的不準看電視;在家吵架斗嘴、在外惹是生非的不準看電視;每天晚上只看一集正片,其他節目不準看。
我至今還記得,我們看的第一部電視劇是《星星知我心》,講的是女主角古秋霞丈夫不幸遭遇車禍去世,留下體弱多病的她帶著五個3至12歲的孩子。古秋霞得知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癥,無奈把五個孩子都送人,這五個孩子的名字叫秀秀、彎彎、東東、佩佩、彬彬,他們的成長之路,收養他們的家庭等等。當時看得我們淚水漣漣,每一集都被電視劇里的人物、故事情節感動落淚。《星星知我心》放完了,馬上接著播下一部連續劇,珠江臺每晚八至九點固定播放電視連續劇,一部接著一部,從不間斷。我們每晚準時端坐在電視機前,雷打不動。
1986年,《西游記》開播,這可把我們樂壞了。每天不管農活多忙,看《西游記》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此后連續幾年,《西游記》一直在反復重播,中午也有播放。有一次,烈日當空,在田地里累得無精打采的我們正在伸懶腰想偷懶,母親吆喝一聲:“中午想不想看《西游記》?”“好呀、好呀!”大家立馬精神抖擻。“那就干活麻利點,早點干完早點回去,等下《西游記》開始了。”隔壁田的鄰居阿饒古說:“你家幾個孩子都在上學,你這么早買電視,不怕影響他們學習嗎?”母親說:“別人家有電視,我們沒有,孩子們去別人家里看被人奚落,我相信我的孩子們會爭氣的。”說完看了我們一眼,我們都使勁點頭,母慈子孝的溫馨畫面像金燦燦的稻穗……
為了看《西游記》,我們開始進行割禾比賽,一大片沉甸甸的稻穗很快就被我們放倒,擼到打禾機旁,母親踏打禾機的腳更有勁了,大家齊心協力,提前完工。想到孫悟空打妖怪的痛快,肩上挑的稻谷也不覺重了。
中午,一家人邊吃午飯邊看《西游記》,姐弟幾個常常開玩笑誰是豬八戒,誰是沙和尚,都爭著想當孫悟空……那時,看電視是我們家最幸福的時光。
(包麗芳,東源縣文聯主席,筆名立方,廣東散文詩學會會員,河源市作協會員,作品散見于《作品》《南方日報》《河源日報》《河源晚報》《梅州日報》《增城日報》《陽江日報》《廣東散文詩學會》等報紙、雜志、公眾號。)
下一篇: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