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與文學間遨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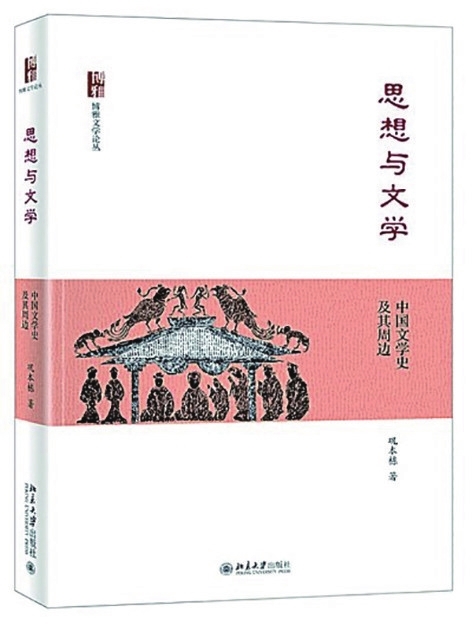
《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
鞏本棟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何謂為文?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在這一為中國古代士人所熟知和信奉的思想體系中,文學寫作,往往被歸之于“立言”范疇,即通過文字著述,表達自身的思想觀念,實現個人的社會價值。
雖然“立言”的社會價值似乎不及“立德”與“立功”,但對于中國古代士人而言,其追求個人主體價值實現的思想內核卻是一致的。于是,作為“立言”之重要一途的文學寫作,或意在言志寄情、申紓性靈,或追求經緯天地、匡主和民,總難免與重道修身、經世致用等觀念交織相融,同構于中國古代包容萬象的思想文化體系中。因此,研究中國文學史,向來無法脫離對相關時代文化背景的闡述。
然而作為歷史文化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自身具有十分復雜的內部情況,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等其他思想文化資源,對不同創作主體的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如果只是泛泛而談,則很難真正把握文學發展的深層歷史脈絡。對于這一點,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鞏本棟的《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一書,在方法論層面或可給予我們有益啟示。
全書時間跨度縱歷先秦至明清,但并不像一般的文學史著作那樣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選取每一時期若干重要文學個案,站在思想文化的宏觀視角,采用考據與批評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于紛繁復雜的時代背景中,抽繹出影響文學發展最關鍵、最直接的外部要素,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思想文化視域。
文學與修身
關于文學與個人德行修養、志趣觀念之間的關系,《尚書·堯典》中已有“詩言志”之說,《毛詩序》更進而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此“志”,一般理解為作者的思想、情志、抱負等,在某種程度上亦可視為作者個人品格操守的文本外化形態。
如中國最早的長篇政治抒情詩《離騷》,即可視為屈原之“志”的體現。詩中所寫“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既包涵了屈原的政治追求,也表明了他一直所堅守的清白高潔、剛正不阿的個人品行,以及固守正道卻遭讒見疏的憂憤。
對于這篇在先秦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作品,無論其內容主旨、藝術風貌,還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創作動機等,歷代論者解讀已多。鞏本棟先生則另辟蹊徑,在本書中著重分析屈原個人情懷寄托的曲折變化過程。通過對《離騷》的文本細讀,鞏本棟發現其思想藝術有一個十分鮮明的特點,即前半部分悲憤嗟怨,“流露出對楚國前途與命運的深廣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具有偏重現實的創作傾向;后半部分則結想宏富,“反映出詩人高遠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及卓異不凡的才情”,即浪漫瑰麗的創作特色。至于轉變的肯綮,正在于詩中極為關鍵的兩句——“退將復修吾初服”與“就重華而陳詞”。前者是詩人現實境遇中理想的失落,通過內轉式的自我疏解,尋求擺脫心理困境的力量,最終選擇堅守正直的品格;后者則結合歷史做出想象,轉而向外,向先王前修尋求支持,堅定“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決心。于是,熱烈無羈的浪漫想象與忠直堅定的人格情操完滿地融為一個有機整體,并且“開創了中國抒情詩的真正光輝的起點和無可比擬的典范”。
文學與治學
《禮記·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作為正心、誠意、修身的前提條件,中國古代士人對于致知、治學的追求,既與個體道德修養有關,又有顯著的“立言”意味,在心理動因方面與文學創作具有一致性。
因此,士大夫文人的學術思想,往往會對其文學寫作產生影響。這一點,在注重文治的宋代體現得尤為明顯。宋代士人學識淵博,格局宏大,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說,多為“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論者亦每謂宋人好“以學問為詩”,因此要研究宋代文學,不可不關注宋人的思想學術。
在《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一書中,有《歐陽修的經學與文學》《蘇軾的思想學術與文學創作》,也有《南宋文化“紹興”與〈宋文鑒〉的編纂》等,其關注重點正在于此。其中,尤以第十一章論歐陽修的思想學術與文學之關系最為典型。
歐陽修在經學、史學、金石學等學術領域皆有成就,經學之中,尤深于《易》《詩》《春秋》。作為北宋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文士領袖,歐陽修治經學最大的特點,便是以人情常理為本,對經義本身進行解讀。至于前代儒生奉為圭臬的傳注,歐陽修則大膽懷疑,對北宋疑經風氣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至于其思想淵源,鞏先生通過考察歐陽修的生平家世與治學經歷,指出這種無所束縛的學術主張,乃是由于其家世貧寒,少無所師,故不必如漢儒經師一般固守師承家法,而能夠學出己見,大膽懷疑。這一點,又正與北宋士人多出于庶族的時代背景有直接關系。
可以說,歐陽修的治學經歷與學術思想,為我們理解疑經風氣何以會在北宋出現提供了例證。而對于研究他的文學創作,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關于經學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歐陽修曾大膽提出“六經皆文”的主張:“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后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在破除了對傳注的迷信后,將六經視為出自圣人之手的天下至文,盛贊其“事信言文”,從文章學的角度對儒家經典進行觀照。
文學與經世
對于古代士大夫來說,通過建立事功實現經世濟民的理想,往往是最普遍的追求,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最直接途徑。而文學,既在政治功用方面被認為具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隋書·文學傳序》)的作用,自然而然也與文人經世思想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而“文”與“用”的關系,也是《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一書的論述重點,其中,尤對北宋時期觀照最多。
北宋的變法與反復,本為革弊圖新與因循守舊兩種不同政風、士風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否主張革新變法,其出發點皆為國計民生,本意在于解決北宋迫在眉睫的社會危機。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變法意味逐漸改變,意氣之爭、政治傾軋等因素也進入其間。對于節操高尚、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士來說,如何在波詭云譎的政治風浪中堅守自己的理想,此過程中,文學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對此,中國文學史公認的大家蘇軾可作為觀照對象。在書中,鞏本棟先生通過對蘇軾屢次遭貶所涉歷史文獻與文學文本的細致梳理,深入分析了的蘇軾的政治理想。若以北宋律令論,蘇軾或確有“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之罪狀。然而若結合中國古代詩歌“興觀群怨”的功能來看,詩歌本有反映現實、補察時政以“風謠歌頌,匡主和民”的傳統。蘇軾寫作一系列相關詩歌,正有“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的意味。再聯系北宋政壇淵源有自的“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傳統,“烏臺詩案”實為一樁冤案。隱藏在那些諷諫詩歌文本背后的,是一位士大夫飽含的對下層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也蘊有其自身矛盾復雜的心態。
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史的發展從來不是孤立的,圍繞在其周邊的思想資源,也并非單純以“背景”的形式存在,而是與文學自身的發展脈絡彼此交織相融,共同形成文化發展、文明推進的合力。
這便要求我們在進行文學史研究時,不能脫離宏觀的思想文化視域。然而具體到文學史本身,正如鞏本棟先生所說:“在眾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因素中,總有一些最直接、最重要的背景因素在起作用,而另一些因素則相對影響較小。”那么,要如何揭示出那些最本質、最直接、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以對文學發展的來龍去脈有更加清晰的把握,同樣是文學史研究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而這一點,也是鞏先生此書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發。
(作者:陶慧 來源:《光明日報》)

